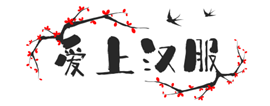不但要跪,还要叩响头,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。只要叩对地方,声音便特别洪亮,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,必须重赂内监,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,且不至大痛。
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
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有一幅五代时周文矩所绘的《合乐图》。一些学者相信,此图正是失传的周文矩版本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一部分。而传世的署名“顾闳中”的《韩熙载夜宴图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,实际上只是南宋人的摹本,其母本应该就是今天流失于海外的这幅《合乐图》。那么如果我们来比较这两幅图像,将会发现:尽管从《合乐图》到《韩熙载夜宴图》(宋摹本)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,但由于画家生活的时代相隔遥远,使得两幅图像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时代信息——这不奇怪,画家总是会不自觉地将自己观察到的时代信息绘于笔下,所以在宋人画的汉宫图中会出现宋式建筑;而在明清画家画的宋朝仕女图中则会出现明清服饰。
先来看周文矩《合乐图》,请注意一个细节:图中的乐伎都是盘膝坐在地毯上演奏音乐,包括擂鼓的那名乐伎,也是用跪坐的姿势。而欣赏演出的韩家宾客、家眷,则多站立,只有韩熙载本人盘坐于床塌,另一名女宾坐在矮凳上。


而到了宋人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,我们看到,五名乐伎都坐在圆墩上吹奏箫笛,一位打牙板的男宾客也是垂足坐于圆墩,韩熙载则在一张靠背椅上盘膝而坐——这个坐姿有些奇怪,也许作为一名老式贵族,他还不习惯垂足而坐。

五代人周文矩的画面,应该比南宋画更加符合韩家夜宴的实际情形,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;而南宋人绘画时,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想象。两幅图像的不同细节,显示出一个信息:宋代以前,即使在贵族家庭,靠背椅等高型坐具还比较少见,人们一般都是盘膝坐在宽大的床塌上,或者席地而坐。
事实上,唐—五代正是椅子逐渐普及的过渡期。而在此之前,中国人是不习惯垂足坐在高脚椅子上的,一般只使用一些矮型坐具,如“胡床”、“连榻”。连榻是可以同时坐几个人的矮塌,《晋书》记载,“杜预拜镇南将军,朝士毕贺,皆连榻而坐。”说的便是这种狭长而低矮的坐卧用具;胡床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小马扎,可折叠,方便携带。北齐杨子华的《校书图》(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,为宋摹本残卷)中就出现了一张胡床。总之,此时中国社会流行的家具,如餐桌、书案、坐塌、椅子,都是矮型的。

入宋之后,高脚的椅子才在民间普及开来。自此,“高足高座”的家具完全取代了“矮足矮座”的家具,中国人从“席地而坐”的时代进入“垂足而坐”的时代。今天我们在宋画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椅子,如南宋画《蕉荫击球图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,图中出现的桌子是高型的,椅子也是高足的靠背椅,从其款式看,很可能由胡床改良而来。当南宋的画师描绘“韩熙载夜宴”的场面时,也会不自觉地画上宋人常见的椅子、圆墩。

跪拜礼的变迁
高型坐具的普及,触发了改变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连锁反应。比如说,在流行矮足矮座家具的时候,大家围成一桌用餐是不大方便的,因此分餐制大行其道;而高桌高椅广泛应用之后,围餐就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了,因此合餐制渐渐取代了分餐制。
还有,传统的社交礼仪也被改写。在只有矮型家具的先秦,人们在社交场合都是席地而坐,正式的坐姿叫做“跽坐”,即双膝弯屈接地,臀部贴坐于足跟,标准姿势就如西安出土的秦代“跽坐俑”。今天日本与韩国还保留着“跽坐”的习惯。

▲ 秦代“跽坐俑”
此时,中国社会通行跪拜礼,因为跪拜礼是自然而然的,由跽坐姿势挺直腰板,臀部离开足跟,便是跪;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,如作揖、稽首、顿首,便是拜。这时候的跪拜礼,并无后世附加的贵贱尊卑之涵义,只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。而且,对方也回以跪拜礼答谢。臣拜君,君也拜臣。许多朋友都应该读过《范雎说秦王》,里面就说到,“秦王跪曰:‘先生是何言也!……’范雎再拜,秦王亦再拜。”跪拜是相互的,是双方互相表达礼敬与尊重。
经秦火战乱之后,古礼全失,汉初叔孙通重订礼仪,“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”,实际上就是糅入了帝制之下君尊臣卑的内涵,诸侯百官“坐殿上皆伏抑首,以尊卑次起上寿”,“竟朝置酒,无敢喧哗失礼者”。所以刘邦在体验了一把繁文缛节之后,不由感叹说: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”后来宋朝的司马光忍不住喷了叔孙通一脸:“叔孙生之为器小也!徒窃礼之糠粃,以依世、谐俗、取宠而已,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,以迄于今,岂不痛甚矣哉!”不过,此时的跪拜仍是自然而然的,因为大家还是席地而坐。臣拜君,君虽不再回拜,却也要起身答谢。
到了高型椅子出现以后,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了改变,跪拜的动作便带上了比较明显的尊卑色彩——请想象一下,你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,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。
也因此,除了“天地君师亲”,宋朝人基本上都不用跪礼,社交礼仪通常都是用揖逊、叉手之礼。南宋时,楼钥出使金国,发现被金人统治的汴京人在接待客人时兼用跪礼与揖礼:“或跪或喏”。楼钥说,“跪者胡礼,喏者犹是中原礼数。”“喏”即揖礼,可见依宋人礼仪,日常待人接物是不用跪礼的。南宋覆灭后,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,蒙元丞相博罗召见,文天祥只是“长揖”,通事(翻译)命他“跪”,文天祥说:“南之揖,即北之跪,吾南人,行南礼毕,可赘跪乎?”文天祥只揖不跪,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带有屈辱、卑贱之意,揖才表示礼节。
我们从多幅宋画中也可以找到揖逊、叉手之礼,如南宋宫廷画师所绘《女孝经图卷》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中有一个场景:皇后与皇帝、大臣见面,大臣行叉手礼:

宋代的臣对君,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,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仪典上,如每年元旦、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、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,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。日常的常朝会也有臣拜君的礼仪,据《宋史·礼志》记录的“正衙常参”礼仪,“舍人通承旨奉敕不坐,四色官应喏急趋至放班位宣敕,在位官皆再拜而退”。但这里的“拜”,跟跪坐时代的“拜”,是不是相同的动作呢?值得考证。我看过宋人王楙就曾考据说,“肃拜,但俯下手,即今之揖也。何尝专以首至地为拜耶?”
再据《宋史·礼志》,淳化三年(992),宋廷申举常参礼仪,将“朝堂行私礼,跪拜;待漏行立失序;谈笑喧哗;入正衙门执笏不端;行立迟缓;至班列行立不正;趋拜失仪;言语微喧;穿班仗;出阁门不即就班;无故离位;廊下食;行坐失仪;入朝及退朝不从正衙门出入;非公事入中书”等十五项行为列为失仪,“犯者夺俸一月”。由此看来,宋臣常参时似乎并不行跪拜礼。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,当是揖拜之礼。
从元朝开始,带屈辱、卑贱性质的跪拜礼才推行开来。治元史的李治安教授根据两则元朝史料的记载:《元朝名臣事略》:“……入见,皆跪奏事。”元人《牧庵集》:“方奏,太史臣皆列跪。”判断出“元代御前奏闻时,大臣一律下跪奏闻,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”。这一礼仪,跟元朝将君臣视为主奴关系的观念也是合拍的。
跪奏的制度又为明朝所继承。据《大明会典》,洪武三年(1370)定奏事仪节,“凡百官奏事皆跪,有旨令起即起”。朱元璋甚至变本加厉,规定下级向上司禀事,也必须下跪:“凡司属官品级亚于上司官者,禀事则跪。凡近侍官员难拘品级,行跪拜礼。”
清代臣对君的跪拜礼更加奇葩,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,皇帝降旨宣答,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。为了避免因为下跪太久而导致膝盖受伤,聪明的清臣发明了“膝里厚棉”的高招:“大臣召见,跪久则膝痛,膝间必以厚棉裹之。”看来清宫戏《还珠格格》中“小燕子”使用的那个“跪得容易”,并不是胡扯。练习跪拜也成了清代大臣的必修课,“光绪某年,李文忠公鸿章以孝钦后万寿在迩,乃在直督署中日行拜跪三次,以肄习之。”臣下如果跪得乖顺,则官运亨通,大学士曹振镛“晚年,恩遇益隆,身名俱泰”,门生向他讨教为官的秘诀,曹振镛告诉他:“无他,但多磕头,少说话耳。”
不但要跪,还要叩响头,以头触地,叩得越响亮越显示出忠心,“须声彻御前,乃为至敬”。据称,清宫“殿砖下行行覆瓿,履其上,有空谷传声之概”,只要叩对地方,声音便特别洪亮,所以大臣叩见皇帝之前,“必须重赂内监,指示向来碰头之处,则声蓬蓬然若击鼓矣,且不至大痛,否则头肿亦不响也”。
不但臣见君要跪拜,小官见大官也必须下跪。清人况周颐的《餐樱庑随笔》说,光绪初年,工部司员见堂官,“鞠跽为礼”,所以有人以《孟子》中
主题授权提示:请在后台主题设置-主题授权-激活主题的正版授权,授权购买:RiTheme官网